文/PP机

我刚和女朋友从这座城市的那边回来,手里拎着新百伦的袋子,把新鞋脱在一边,仰头靠在沙发上无所事事。
昨天这个时候,傍晚六点左右,家里的玻璃上打着细密的雨,屋外天空是褪色的宣纸颜色。我捧着刚买的海明威文集准备消磨一晚上。
手机在我伸手碰不到的地方,我不希望它打扰我的生活,但是昨天这会它极没礼貌地响起来,打断了雨天的气氛,我费劲地弯腰去拿手机,海明威哗啦一声合了起来。
手机屏上是一串我一年都没有见过的手机号码,前女友的手机号冷冰冰地在我屏上闪来闪去,我吸了一口气,划开屏幕。
“嗨。”
“嗨。”
之后是意料之中的一阵沉默,好像是我打电话找她一样。
“有什么事么?”我用最陌生的语气问她。
“有,能来一趟么。”她平淡地回答,好像轻松递给我一片口香糖一样。
我绝不是那个前女友一个电话就不知所以的人,于是我问她
“有事?”
她那边似乎妥协了。
“有,我家这边,有人跳楼自杀了,一个人在家里有点害怕。”她的语气依旧平淡得像个句号。
我说我现在去,叫她不要害怕。
我失望地看了一眼海明威。
我伸手拿起搭在沙发上的冲锋衣,把拉链拉到顶头,耳朵里匆匆插上耳机除了家门。一出家门雨的气味就往鼻子里钻,我慌乱地按了几下耳机线上的线控,指望下一首随机播放的歌曲和我现在的心情走在同一条轨道上。家门口几个老人抱着胳膊望着门外昏黄,冒着雨的天空,好像这场雨打断了他们散步计划。我从他们中间挤出来,一头扎进雨里。我从来没有打雨伞的习惯,雨伞是留给我妈和右手边的女孩的。
雨水从我脸上匆匆划过去,和我背道而驰赶去见不同的人。
我想起来和前女友的头一次见面。那算是一次可以作为谈资的浪漫经历,可是我却第一次写出来。
去年再晚些时候,宿友约我去近郊参加本地小有名气的音乐节,我宿友的头发总像上一秒刚被大风蹂躏过一样凌乱着,他说这样很摇滚。
我们那个周末坐大巴车到近郊很大的一块人工草坪上和人群一起等待音乐节开始。音乐节是属于音乐和阳光的,那天主办方似乎过分相信了天气预报,还没等开始就下起了蒙头细雨。宿友本来是期待看见姑娘们在草地上伸长她们的玉腿,可是姑娘们却瑟缩着抱着雨伞,对于他来说他完全浪费了门票和车费。我瑟缩着插着兜,百无聊赖地环顾着穿着同一款潮牌的男女,同一副表情的人群。然后你猜到了对么?我看见她了。她自己撑着伞,浅蓝色及脚踝的长裙下面是匡威纯白色的帆布鞋,上身简简单单的一件白色衬衫,整齐的发帘刚刚盖过眉毛,长而不过肩的发梢温柔地向上卷着。她目光迷离地看着人群。她是人群之外的她。
“那是我高中同学”宿友搭着我肩膀,叼着烟。
“你想泡她的心情我理解,就像我想泡我初中那成天穿黑丝的班主任。”说完他就狂笑起来,把烟都吐到我脸上。然后他搂着我肩膀把我拉过去,“走吧,给你介绍介绍。”
她看见他走过来,微微点头示意,好像他们昨天才见过面。
我看着她面对的舞台,要演出的是一个才组建的小乐队,我冲她笑了笑,问她“喜欢摇滚?”我还没说完话宿友就逃走了,我一整天都没见到他。
“也不是,宿舍里太闷,出来透透气。”我点点头,脑袋里转着下一句答话。
我就这样跟她打着雨伞和她从中午断断续续地聊到傍晚,我和她说女孩太晚回家不安全,早点送她回家,于是我们在音乐节散场之前就离场了,离场的时候雨还自顾自地在重金属和尖叫中下着。
我坐着大巴一直到城市边缘的中转站,我坚持要送她回家,她只是摆摆手,我说那至少也要留一下微信。她看着我,说只有QQ,而且不经常用,我说那就留一下吧。作为礼貌我也留下自己的QQ。她翻着跨在肩上的藤制编包,找出一个印着她大学名字的本,翻了几页,抄了一行数字留给我,解释说上面是QQ,下面是手机号码。我笑着说你当我傻啊,数字个数都不一样。她看看我,说她不太了解。于是我眼看着她雨一般朦胧的背影离我远去。
我瞬间松了一口气。
我从未觉得聊天让人身心疲惫。
等到我夜里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了,我一头砸在床上,当我意识模糊的边缘时,我才意识到,城里根本没下一滴雨。
也许今天的雨是对一年前的补偿。
我一手拖着自己下巴看着窗外,一手抠着裤子上的线头。她家在城市的那头,而我的大学在城市这头,在城市对角线的两端,由于她不用手机,我们真的在谈恋爱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谈恋爱,我有时候甚至觉得她这辈子也不会再联系我了,我也觉得这样挺好。只是去她家的途中我是很惬意的。我总能放下所有的事情,专注地望着窗外走神。
从老城区到新城区,从筒子楼到玻璃墙的大厦,这座城市的一切都让我着迷,它时常让我想起自己的城市,我恍惚间觉得下一站下车就是我家了,爸妈在家里等我吃饭。
今天雨点细碎地打着公交车的玻璃,把车外红绿的车灯支离破碎,眼前仿佛装上一支万花筒。
我看着窗外零星色色彩逐渐迷离,听着公交的引擎声逐渐远去,我安心地睡过去,她家在终点站,我从来不应担心做错站。
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打开微信却是QQ的界面,梦到我和全部的朋友都失去联系,梦到我的好友列表里只有前女友一个人的名字。
她找我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情。
我半睁着眼睛看着屏幕上一条未读信息,蓝色的标,脑袋里想起来几个依旧用QQ不用微信的朋友。我划开屏幕,上面简简单单一条信息让我彻头彻尾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做我男朋友吧。”
当时的感受就像硬被陌生人塞了厚厚一信封的钱,第一反应是要还给人家。
“其实我无所谓啦,但是你能接受?毕竟我们没聊几句,你也许还不算了解我。”
那边过了快一分钟才回复。
“中转站见一面?”
就是那天我第一次去了她家,成为她们家来的第一个外人。等到我们快分手时我才知道,那天她迎来自己的初恋,20岁。
Betty(第一次认识她时我们一同参加大学英语系年终表演,她演的女孩叫betty,后来就一直这么叫了)的电话把我拽回雨淋淋的世界,她不加问候语地问我
“明天陪我去配情侣鞋!不许说不!”
Betty是那种笑容像是从阳光里鲜榨的女孩,她能把你所有的烦恼都融化在她的阳光里面。
“好!我可为这双鞋攒了三个月前呢!”
“在干嘛?”
“见个同学,马上回宿舍。”
“哦。。。又没带雨伞吧!再感冒我可不给你洗内裤!”我在公交车上就笑了出来。
到她家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
我每次在她家楼下徘徊时,都隐约希望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去她家,只是不忍心证实罢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竟然下意识地走进她家楼下的西点店,那瞬间我并没想到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需要像往常一样再给她买两个蛋挞。我既然跨进来了,就拣了两个蛋挞排起长队,也许是因为不想这么快见到她。
我想起头一次和她来这时,我和她坐在店里唯一的一套桌椅对面,她说要吃两个蛋挞。买完后我像第一次和她搭茬时那样问她
“喜欢蛋挞?”
“嗯,以前妈妈常做。”
“阿姨好厉害,现在也常做?”这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在犯傻。
“他们死了。”说完,她咬一口脆皮。
我看着她。
“她们以前也是开西点店的,“她自己说起来,“我五岁那年,店里发生事故,烤箱爆了,飞出来的铁架子把他们砸死了。”
我不确定该说些什么安慰她,我自己也是一惊。于是捏捏她放在桌子上的左手,摸到她脉搏位置有一个食指长短的伤疤,
“怎么搞的?”
“那次炸出来的玻璃划伤的。”于是我做了也许是我这辈子最伤人的事情,我猛地把手抽回来,就像是突然被烫到。
后来,我看着面前的女孩,走上前抱住她,我只是想抱着她,如果能够给她一点安慰也好。
我后来和她邻居聊天才知道她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她高二的时候爷爷奶奶就相继去世了,于是她一直自己一个人生活。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非常害怕。说不出原因的害怕。我知道对于她来讲自己很大一部分是多余的,我无法搞清楚她安静的面容下面有多枯槁。
是的,我是说,有时候我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女朋友是谁。
我拎着两个温热的蛋挞往她家走着,雨还在下,像是劳累工人一样夜里也不肯休息,只是闷头下着。院子里除了雨声很安静,她家后院是一大片苗圃,以前总喜欢和她去里面坐一坐,大多数时候是我望着她白色的帆布鞋发呆。我意识到她的小区也许根本就没有人跳楼,她只是想用这个理由来见见我,我想到这竟然有点生气。
她家在25楼,她有一次我和说她小时候最大的爱好就是趴在自家楼顶上吐口水,看自己的口水消失在视野里,当时我不无悲伤地想这件事一定发生在她5岁之前。
到她家的时候我敲敲她家已经生了几层锈的防盗铁门,没人响应,我想她可能是睡着了,我记得她床头那些生涩的原版名著。于是我像上次一样用埋在她家门前地毯下的钥匙开了门。
她家里时黑的,一阵灌堂风吹的我一阵瑟缩,我把灯打开,家里像我上次来的时候一样整洁的像没人住过,只是房间里老旧的陈腐味道被那阵风吹的淡了一点。
我叫了一遍她的名字,没人回应。
我向她我是走过去,看见她卧室那条白色麻布的窗帘湿辘辘地粘在墙上。
我头皮顿时一阵发麻。
然后我坐在她床上,看着窗外一刻不停地柱般地雨。
我把窗帘拉进来,光好窗户,关上灯,锁上门,踏齐门前的毯子。
向她每次离开家那样。
你也知道她在哪了。
只是我不想承认罢了。我下楼走到她窗前正对的苗圃。
看见她像一张揉皱的卫生纸般被丢在水里,隐约看到地上汩汩的暗红色留向四处,流向我。奇怪的是她那 双白色匡威却一点也没脏,在夜里泛着光。我打电话报了警,在警察来之前的半个小时,我像之前无数个夏夜那样和她一起坐在苗圃里,谁也不说话。
我想她有很多原因自杀,可以说支撑她活下去的因素很少。
我隐约看着她头发凌乱地随雨水四处飘动。然后我眯起眼睛看看夜空,看看她卧室的窗户,但是我看不到她的视角。她是什么时候自杀的呢?发短信之后五分钟?十分钟?
我不清楚,我只知道那个自杀的人,是她自己。
警察来了之后处理尸体时我转过头去,看见她被装在另一个车里匆匆离开了她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我和警察去做笔录,看着黑暗一点点吞噬这座楼的轮廓,我突然意识到她完完全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一块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没有一滴属于她的眼泪,她的名字明天就会被她的导师划掉,我也突然明白她为什么叫我来,她害怕离开这个世界时什么也不剩下,于是她想在我的回忆里留下点什么。
再次坐公交车回家已经凌晨了,车上空荡荡的就我一人,开在空荡荡的城市里。就在我快睡着的时候,手机突然响来,突兀地像下午她的电话。
是她么?
那瞬间我浑身酥软,整座城市的寂静把我逼得窒息,我真的没有勇气拿出手机。
手机停了,世界再次被寂静统治。
我慢吞吞地拿出手机,一个未接来电和一条微信。
It's a wonderful world,像歌里唱的那样。
是Betty.
她提醒我洗个热水澡,别忘了和她去买鞋。
这时候我才发现雨停了。
雨停了。
夜色静静的被我甩在身后。
原载: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21537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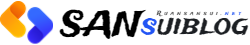



失落的羊9 个月前
研究计划导入公众号文章。
失落的羊1 年前
研究插件:挂载点研究、文件读写研究、API读取数据、设置、前台显示
失落的羊1 年前
今日申请十年之约博客成员!
失落的羊1 年前
启用新的访问统计.
失落的羊1 年前
重新整理长篇连载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