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高富帅的那一年
文/午歌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身高已经惊人的蹿到了1米75,站在篮球架下,我一跃而起,双手的指尖可以轻轻的划过篮网。那时候我瘦得好似一副风筝架子,为了和普遍比我矮半头的同学协调混搭,我在走路时拼命锅腰,好似一尾水中游弋的“虾蛄”,这种常见的海洋生物,在北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富贵虾”,可是用我们的土话喊出来却是——“拉尿虾”。
那天我站在男厕所的台阶上一边思考,一边小便,用强劲的尿柱在墙上一会儿画出“一”字,一会儿画出“人”字。同班的磊子,跨上台阶,窸窸窣窣的解开衣服,触电似的边尿边摇晃得厉害。我搭眼一扫,看见他粗短的小吉吉上,浮着一层黑涔涔绒毛,像茂密的胡渣似的,散发着一种成熟的雄性魅力。
视线很快转移到我身体的同样部位,这里一片荒芜,干净得像雪后的晴空。磊子白了我一眼,得意的笑起来,哆哆嗦嗦得的竟然将他还在出水的神器收进了裤子,随即腿上又是一阵急促的哆嗦。
“操,还没尿完!”
磊子迅速又掏了出来,双手忙活着一阵拷问,然后打完收工,嘴里嘟嘟囔囔着:
“哎,午歌,你怎么还没发育呢?”
这话戳中了我的自卑,于是我草草完成我的画作,淡淡说:
“少管闲事!”
磊子是我的最佳损友,和我同在校运动队,他的专项是百米,而我练篮球。他上五年级那年就能和初二的学长跑得一样快,而我虽然是全队个子最高的,却常常在比赛中打不上主力。磊子很帅,高鼻梁,大眼睛,头发乌黑发亮,最重要的是生来就有点自然卷,在那个费翔老师用“冬天里的一把火”燃烧了整个赤县神州的年代,“自然卷”这种抒情的发式,安静的撒发着天然而高贵的优越感。而我除了海拔略高之外,在他面前似乎一无长处。
当然这样的差距还有很多,比如:磊子他爹是桥梁工程师,满世界的出差旅行,满世界的给他买各种漂亮衣服和帅气的运动鞋,而我爸爸是一个木匠,对,一个木匠!我家后院里时常堆满各种粗圆的木料,房间里长年飘着一种木屑的味道,各种大小、各色样式的柜子,整齐的码在前庭。
对了,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爸常常告诉我,他制作的柜子,其实是一种神秘的时光机,人钻进去,关上柜门,时间就会飞速的流转——以至于你在柜子里坐了很久,开门出来的时候,发现时钟其实只走掉了小小的一格。
这事儿我在童年的时候一度信以为真,因为我每次被我爸一阵怂揍之后,他会把我仍进他的柜子。在那黑暗无光、满是木屑味道的时空里,我哇哇得哭上一炮,最后我爸打开橱柜的门,淡淡的问我,想通了没有?我委屈又无奈的点点头,擦干眼角的泪水,吸回上唇的鼻涕,兔子一般的从柜子里蹿出来,—看看时间——哇塞,原来真的不到十分钟,可为什么会感觉有那么久?
扯得有些远了。大家一定在少年时有过相似的经历,当你遇到一个帅气、土豪又发育得良好的同学,而他恰巧又愿意和你做小伙伴时,你们自然很快会鬼混在一起,成为亲密无间的损友与玩伴。虽然,已不如人的感觉偶尔会跳出来作祟,可“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的虚荣心,迅速会将自卑心干翻在地,然后事逼兮兮的觉得:“we are a team!”整个人生也浑然臭牛逼起来了。
每天放学我都会和磊子走在一起,他矮我半头,而我愿意为他弯曲半条脊椎。校园里常常会有女孩子向磊子投来羞涩而真诚的微笑,那些笑容的波长很大,通过空气传递,在磊子的脸上漫反射之后,也会在我心中荡起层层的涟漪。
我喜欢隔壁班一对姐妹花的微笑,高一点的叫马晓,矮一点的叫沈玉。马晓扎一个马尾辫,看上去清新爽利。沈玉扎着两个马尾,看上去双倍的清新爽利。马晓和我的情况差不多,虽然个子略高,上肢却平庸又淡薄,穿着紧身的背心,些许佝偻的身体,像一截稚嫩的竹板。沈玉则圆润很多,胸部微微发育,小巧而紧致的罩杯把她照顾得如同一款包装精致的糖果。两人同时启动微笑,而我很自然地将目光和沈玉纠缠在一起,她会不自觉地脸红,我也会,我会心跳加速,我猜她也会,这是我们之间一种不可言说的默契。
然而马晓会更大胆一些,她常常在抿嘴发笑时,配以锐利的鼻音,那是介于“哼”和“哈”之间的一个音节,然后重复两次“哼哈、哼哈”,既让人明确的知道她笑了,又会让你觉得她笑得矜持又斯文。接下来,照惯例她会和磊子开一个玩笑,嘲笑他自然卷的“鸟窝”头或者花纹奇特的耐克鞋。但她不敢笑我,从来不敢,我以我俯视的目光象征性的扫视她的脸颊时,她也会意外红脸——这让我觉得有点尴尬,因为在我心里,我和沈玉才是幽微无言的一对。
有一次,校队打比赛,磊子、沈玉和马晓都在场外观看,我抢到后场篮板,一路带球突破杀进前场,起三步时,被对方球员撞倒,在加速坠落中,我将球迅速抛向空中,然后狗啃屎一样的重重倒地。球在篮筐上颠了几下,最终还是掉在对方球员的手里。
“午歌,他妈的为什么不传球?”
在我从地上爬起来的瞬间,在队友和教练的责骂声里,我看见沈玉惊得捂上了双眼,而马晓上了发条似的,可劲地高频地输出着她的掌声。
赛后,我搭在磊子的肩膀上,一步一瘸的滚回家中,马晓和沈玉迎面走来。我有些羞愧的不敢看沈玉的眼睛。马晓则很奇怪的没开磊子的玩笑,只是淡淡的对我说:
“虾蛄哥,其实那个球很棒啦!”
天哪,在我人生灰黯无光的时刻,她居然没有用土话叫我“拉尿虾”而是在我的学名“虾蛄”之后,有情有义的加上一个“哥”字——好意外了有木有?!“虾蛄哥”——就好像行走江湖的途中,看到一帮子臭要饭的在晒太阳,忽然双手抱拳的惊呼一声:“丐帮的朋友,你们辛苦了!”——好善解人意,有木有?!
我在马晓难得的柔声细气中,还是将目光锁定了沈玉美丽的身影。可那天她究竟什么也没说。
几天后,磊子找我去上树薅桑叶,说是要送给一个女孩去养蚕。
我问:“你打听到哪里有了吗?”
磊子说:“咱们语文老师石春梅家的后院就有!”
我说:“那我不去了,怕被老师揍!”
磊子说:“你不去,我就把你下面还没长毛的事说出去!”
我说:“那咱们上语文课的时候溜出去薅,好不好呀?”
磊子说:“就知道你小子一定有主意!”
我说:“去的时候,带个篮球!”
磊子说:“带毛篮球啊?!”
我说:“石老师回家看见树上的桑叶被撸光了,一定会追查的,但是应该不会怀疑那一对翘课打篮球的小伙伴吧?”
磊子说:“就知道你小子一定有馊主意!”
就这样我和磊子翘了语文课去语文老师家的后院薅桑叶,折腾了两大包回来,挂在男厕所的瓦房顶上,又赶在下课之前,捧着篮球晃晃悠悠的从后门溜进教室,向语文老师自投罗网。
出人意料的是,石春梅老师正在讲台上正襟危坐的念着我的作文《爸爸的时光机》,看到满头大汗的我,石老师忽然停了一下,指着后黑板说:
“这篇想象力很丰富的作文,就是最后排那位逃课打篮球的午歌同学写的。”
同学们齐刷刷的扭头向我投来诧异的目光,我登时傻在半空,心中对石老师的知遇之恩感激得无以言表。磊子把脖子窝在课桌里,扭过头,嘟嘟囔囔的说:
“操,是你写得吗?啥时候炼出了这文笔?”
接着,磊子又翘了数学课,屁颠的屁颠的从男厕所摘下桑叶,冲进操场。我蹲在教室里的最后一排,从门缝里,远远地看见磊子把两包桑叶塞给了马晓,一颗心终于安定了下来。
磊子回来后对我无限感恩。他说,多亏了我的好主意,才帮他达成心愿,但是,好人要做到底,今后代他写情书的事,我就要包圆了!
我本想推辞,想到了沈玉和马晓的关系,想到了磊子还会拿那天厕所的事来要挟我,于是爽快得就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我帮磊子写了两个月的情书。春天尾巴上的时候,《唐伯虎点秋香》在学校附近的影院上映了,磊子说,让我陪他和他喜欢的女孩子们一起去看“唐伯虎”,我又一次爽快的答应了下来。
磊子说:他会穿上他爸从美国给他买来的大风衣,他让我也收拾得利索点儿,别给他丢人。我溜回家中,心头小鹿打滚,在家里翻箱倒柜的折腾了好一阵,最后我找出了我爸的一套西装——那是我前年小舅结婚的时候,我妈买给我爸的,而我的身高已经逼近1米8啦,我完全值得驾驭起这样一套拉风的玩意。再没多想,我迫不及待换上了我爸的西装,而更让人惊喜的是,西装的上衣口袋里,居然藏着一张50元的人民币。
我大步流星的走出门外,春风柔柔得滑过我的脸颊,阳光在我的脑门上闪闪发亮,我将手插进贴身的口袋,真实而有力的揉搓着这一张50元的大票,我觉得我的人生,从来没有这样高大过,帅气过,富有过!
红星影院的门口,沈玉和磊子已经提前到达,沈玉捧着一小袋糖炒栗子,磊子抱着一个中筒的爆米花,不停的撸起他的美国大风衣的袖子,查看手腕子上的时间。他们对我这样伟岸的形象熟视无睹,让我觉得多少有点尴尬。
最后,还是沈玉打破了尴尬,在大家为数不多的接触中,一向沉默少言,温文尔雅的沈玉,终于跟我正式地说了一句话:
“要不,你在这儿等马晓吧,我们先进去了?”
“我们”——磊子和沈玉点头示意。我最后一眼望向沈玉,她吐字明白又轻快,就是这简单的几个字,像带着锯齿儿的钢锯条一样,一点一点,彻底割裂了那些曾经无言的默契——为什么不是我和她,不应该是“我们”才对吗?
风忽然停了,房屋斜斜的影子趴下来,人们安顿了,街上再没有嘈杂声、叫卖声、汽车喇叭声,我的腿甚至有点不自然的抖动起来,阳光分外的暖,额顶的汗水,一层层的渗透出来。
马晓终于还是来了,虽然穿着长裙,可还是连蹦带跳的跑了过来。她靠近我时,我意外的发现她穿着一条粉红色的吊带文胸,浮雕式的花纹,连同虚张声势的罩杯在月白色的衣襟里上下扑腾,像心跳成像的光学造影。
“她一定是因为屡次试穿文胸而耽误了时间!”这样想时,我迅速对她滋生了好感——“要是她此时再喊我一声虾蛄哥,我今天一定做她牵手离开的男嘉宾!”
对,就是这样!
“给我们来个最大筒的爆米花!”我对服务员说!
走出影院,已是黄昏时分。
正像唐伯虎点中了秋香,而沈玉和磊子自称“我们”一样,佳人眷属,美好爱情的大结局总会给人长久的温暖。
马晓忽然说:“好帅啊!”
“你是说唐伯虎吗?”我显然明白马晓是在夸赞我西装革履的样子。
“不!是你刚刚买爆米花的样子,阳刚劲儿十足,真的好帅!”马晓斩钉截铁的说:“那感觉,比你罗锅着腰走路帅,比平时打球都帅,比你穿着西装还帅!”
我憨憨的笑笑说:“所以,你是那个负责传递桑叶的女孩!”
马晓说:“所以,你是那个代写情书的男孩!”
我大惊,忙问到:“你怎么知道?”
马晓说:“沈玉给我看信上写‘你头顶扬起的马尾,像我出手的三分球弧线’时,我就知道是你啦!”
余晖斜斜,橘色的阳光打湿了柏油街道,透出一股果粒橙的味道,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居然邀请了马晓去我家小坐。
在前庭的大柜子前,我生平第一次有点自豪的向马晓介绍了我老爸的时光机。
可没成想正说着,我居然听到了爸爸从后院开锁进门的声音。
为了不至于让我爸发现我偷穿他西装的糗事,免于一顿怂揍,我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拉着马晓的手,跳进了我爸的大柜子里。由于情况紧急,我完全没有体会到第一次握紧少女手指时的那种冲动、热切和无以言表的美妙,由于情况紧急,在我听到我爸“嘭”得一声锁门离去之后,我的手还是紧紧的和马晓攥在了一起。
如果这真是时光机该有多好,我们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躲在里面,纯粹的黑,纯粹的喘息、纯粹的心跳,任凭时光飞逝,就这样手牵着手,在青春萌动的一瞬间,走完一辈子,白头相老。
马晓在我胡思乱想时候,将手迅速抽了出来,我猝不及防,被她用力向前一带,倏然向她倒过去。我在撑住木柜门的瞬间,闻到了一种悠悠的味道——那不是木屑味,是香的,甜的,若有若无的。我得脸颊迅速红热起来,在抬起头的瞬间,擦到了马晓比我更为红热的脸颊。
就在那时,我猛然推开时光机的木门,快步冲向了卫生间。
可是我尿不出来。我惊恐得认为我病了,那是我从未体验过的人生经历,两腿之间不再细软,仿佛石化了一般,变得木然、坚硬、挺拔。
我用双手不断的拷问,纠结,借着黄昏幽微的光火,我惊奇的发现,我从前如雪后晴空一样干净的处女地上,不知何时竟生出两根黑丝,他们打着卷,倔强的向上生长着,像一对坚挺的问号,像磊子头顶自然卷的长发一样,散发着天然而高贵的优越感。
我长长的舒出一口气来,不管怎么样,在我正式成为高富帅的那一年的春天,我在老爸亲手打造的时光机中飞速脱胎换骨,而终于,悄无声息的,发育了。
原载:http://www.douban.com/note/453617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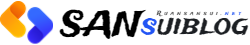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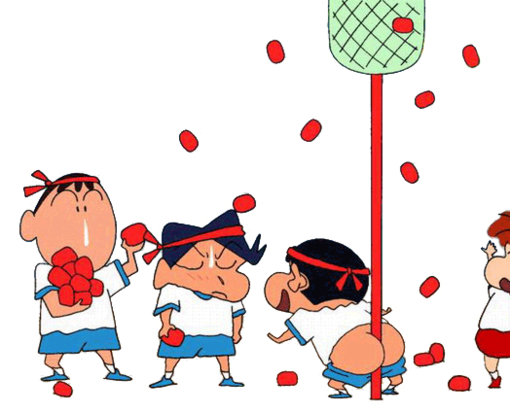

失落的羊9 个月前
研究计划导入公众号文章。
失落的羊1 年前
研究插件:挂载点研究、文件读写研究、API读取数据、设置、前台显示
失落的羊1 年前
今日申请十年之约博客成员!
失落的羊1 年前
启用新的访问统计.
失落的羊1 年前
重新整理长篇连载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