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静波宁任逍遥
世上有很多人会顺利告别青春,让曾经流着的鼻涕渐次风干,然后用一种戏谑的眼光打扫干净残余,成功地欢迎胡子拉碴、满身烟草和酒精味道的那个男人的尊驾;或是庆幸在各种化妆品的涂抹下掩饰被岁月风尘挫败的娇嫩容颜,欢喜接纳作为一个成熟女人的代价。接下来时光继续笑纳了沉重的欲望、滋长茂盛的胡须和鱼尾纹、并培养粗俗的情趣,在自怨自艾中愁对两鬓的斑白及无奈的衰老,最终死去。但并非每个人都是如此,有人并未老去,却早早夭亡……
陈庆阳属于后者。今天他二十一岁。四年前的那个秋天他还在比这里稍北的湘赣交界处的小镇上高中,觉得自己像一株压抑在石缝中的弱草,一边狠狠地憎恨着刻板的高三生活,一边不放过任何机会憧憬四月的杨絮和欲望一起纷扬。他曾经在美术课上画了一个窗子,密集地竖着铁栅栏的那种,透过去,外头是教室里经常看到的那棵偌大的樟树,自如吐纳生机,汲取阳光和空气。在这里寄生自己下巴上正悄悄滋长的淡黄色体毛,以及心中某个阴暗角落里随时准备一场暴动的情绪和欲望。这个秋天他还策划并自导自演了一场标准肥皂剧般的真情告白。期间不乏心怀叵测、鬼鬼祟祟、忐忑不安,凡此种种。最后让长久的失落彷徨占据了关于那个秋天整个的记忆。来年夏天,他南下广东。
陈庆阳觉得十七岁那年真的是道坎,发生了不多的几件事,却带着决定性的意味。之前的一切就像春天密林里的游丝,倏忽飘摇,变得疏隔不可触及。那之后的自己,彻底掐灭了身体中四处萌动的各种憧憬,真真正正地在更南边的都市风尘里埋头打拼,获取吃食,再也没有临窗眺望些什么的雅兴。
夜色温柔。经常在收音机的夜话节目中听到这句开场白。女播音员用带着肉欲的甜腻语调,开始伊甸园里的启蒙。陈庆阳经常在这样的声音里试图找回星点属于自己的放纵青春,然而总是在深入海底的疲倦中迅速睡去,度过又一个无梦的夜晚。
在云梦山上,这个城市的至高点,莞城的夜繁华一览无余。不断新设的工厂和工业园区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日益庞大的人群和不断滋长的城中村,也彻底调整了城市的生物钟。白天人们从笼子一样密集的群租屋中汹涌地挤占总是逼仄得可怜的街道,奔向公交车站,奔向工厂区。随后街道上除了隔夜的避孕套、塑料袋、呕吐物以及各种食物残渣,就剩下三两只交配打斗的流浪狗,冷清得有些瘆人。太阳每天照常升起,工厂区靠林立的烟囱和机器催情狂躁,而都市区总是在昏昏欲睡中苦苦等待着夜晚的苏醒。此刻,陈庆阳静静地坐在山顶的观景露台上,吹风,看眼下的都市区在初上的华灯下渐次复苏、兴奋和高潮。
他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托一个亲戚介绍,在小饭馆里当杂工。有一天拿起水桶里的一条鱼正要去刮鳞,不经意中看见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少东家”正念着高三语文课本里的一篇熟悉的课文,是陶渊明那篇《归去来》,猛然间觉得手中的鱼和自己一样命若飘萍,无从决定,没得选择,悄悄掉下一滴清泪。
陈庆阳现在做的工作在一家台资企业,流水线上焊接手机电路板。那些细若针孔的焊点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半个手掌大的线路板上。这个工作他做了三年,现在已经有些游刃有余。相比一天下来十二分酸胀的腰肌,更难捱的还是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有一段日子,他的耳朵里一直发出不紧不慢的空调滴水的声音。他于是默默地数,数完一万三千六百十四声吃中饭,下午稍稍多一些,一万八千四百零七,正好当班的课长拿起挂在胸前那个看起来已经向黑色蜕变的黄口哨。某日回到宿舍一问同事,其实关于滴水的数目竟然冒出了三四个版本,让他大为惊讶。一笑过后,各人依旧数着各自版本的钟点,继续焊接那些细得要命的手机线路。
线长是个本地女人。向她请假上厕所要重复两次,一次预先报备,一次恩准排队。且一天不能超过四次。大家都管她叫催命鬼,名副其实。陈庆阳就因为私自上厕所已经被她上告两次。所以陈庆阳现在其实不期望过多的尿意信号,他更强烈地希望自己再生一场类似高烧感冒之类的病。上次有幸被请进了厂里的医务室,正赶上SARS流行。厂里从老总到基层线长一体高度重视,关怀备至。他叨恩在这个只和车间一墙之隔的室外桃源挂了三个半天的盐水。这个七八平米的小房间被灰蓝色的破布帘隔成两半。他躺在帘子后面的钢丝床上,身下的竹席汗斑点点,发出阵阵人体油垢混杂着狐臭、汗臭的复杂气味,总让他做一个关于重庆的梦。他从喧闹的牌九桌上撒身撤退,背后是手持三角刀、捋起袖管、头冒油汗青筋的袍哥弟兄拔腿追赶。在那些逼仄郁热、盘曲回转的弄堂里,怎么也钻不到尽头……醒来后心宽意懒,通体舒泰。想想这竹席一定阅人无数。躺在这里的人心情大抵如他。隔壁机器轰鸣,人头忙乱,这里倒先不忧心病情,还是尽管兀自全身心地享受这片难得的闲情……
就这样捱到今天,他二十一岁。早晨陈庆阳打电话给阿云。“哦,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电话那头阿云睡眼惺忪,略显沙哑的嗓子透出经夜不眠的疲累。陈庆阳已经习惯。这个点,她应该刚从夜店或者某个男人的怀里回来,在顶楼的平台上对着前面一汪漂浮着方便面盒子、死鸡死鸭的池塘喷一口漱口水,刷牙,然后一头栽在小铁床上昏昏睡去。但三天前陈庆阳就已经告诉过她要她陪自己过生日的,她还是把整个夜晚的身体和热情给了夜店、陌生的男人和酒,却在他满心期待的早晨里抛过来一声冰凉的祝福。虽然莞城的秋天并不冷,但此刻陈庆阳却久违地对哪怕些许柔暖的体温有点小期待。久违的期待落空,让陈庆阳四年来第一次感到沁心的寂寥和寒凉。
连他自己都有些奇怪,自从父亲去世,这种细微得矫情的感觉早已经很陌生了。那年坐上南下的长途汽车,母亲的嚎啕哭泣只让自己心烦。没有初出乡关的悲情,也没有牵恋思亲的切痛。他使劲别过脸,瞧着清晨黛色的远山,决绝地真想一去不返。
其实他和阿云一样明白,彼此在一起只是在这座无所托付的城市中间寻找对方身上那份稳定的情欲和肉体的抚慰。除此之外,阿云还喜欢陈庆阳烧的一手湖南菜。烧菜纯属无师自通。他会掌握火候,会准确拿捏咸淡。颠锅的时候,总是弄得满屋浓香,让人垂涎不已。
周二是他们约会的日子。阿云虽然时间上可以自己决定,但周末是生意最忙的。而周二,刚好陈庆阳下午调休。就这么决定了。周二的下午陈庆阳会先去菜场买上一条非洲大鲫鱼,一斤小龙虾,还有猪肉以及一些时令的小菜,当然辣椒必不可少,再去便利店买些啤酒。然后开始在自己租住的小屋子外面支起液化气灶,杀鱼、择菜忙活小半天。看看暮色四合,陈庆阳开始炒菜炖鱼。阿云总会挑时间,她一直是踩着饭点进门。
褪去了平日里取媚恩客的那身浓妆,一件素色的连衣裙或者外面套件开西米,显出湘妹子娇小玲珑的身段。阿云的脸盘圆润,一双水亮的大眼睛总是眨巴眨巴地凑上来显出一派青春期少女的好奇。初见阿云之前,陈庆阳这还是童子身。除了听着广播的夜话节目入睡,他再没有关于男欢女爱的任何奢想。那年和一帮厂里的小弟兄发过年终奖又不用回家过年,整日喝酒打牌鬼混,终于被撺掇着紧张兮兮来到一家洗脚店。他第一次踏进混杂着沐浴香波、廉价香水以及若干体液味道的暗红色空间,和阿云迎面撞上,借着未消的酒力昏昏花花,仿佛一下子穿越时空,回到原本有些疏隔了的十七岁,在秋天校园里略显丰盈的广玉兰花瓣下,切肤感受到杨絮纷飞的四月,沉迷于再也无从把控的肉体温存。
“没回家过年啊?”阿云一口略带娇羞的湖南腔普通话把陈庆阳从四年前拉回到现实。“你也是湖南的?”“嗯,你湖南哪里咯?……”女孩说话少有久经风尘后做作的热情。她眨巴着那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一字一顿地聊家乡、聊湖南菜、聊自己的经历。直到老板娘敲门催客,他们才意识到彼此这种意外的热络已经超出了一个小姐与恩客的关系范畴。他额外拿出两百块,“这个给你,做压岁钱”。说完,两个人都笑了。陈庆阳起身出了店门,一帮弟兄老早完事先走。他寻思着这下回去要让他们好一通取笑了,不觉拐出那条弄堂,来到西河街上。刚要过马路,背后阿云叫了声“帅哥”。陈庆阳回头,阿云拿着一张小纸片小跑过来,“这是我的手机号码,我叫阿云,常联系啊。”陈庆阳还没来得急答应,阿云已经撒手回身,往小弄堂里跑了。
他们成了朋友。春节里,陈庆阳拉上阿云,去了一趟广州的花市。他打算给阿云买一束玫瑰,想想有些唐突,懵懵懂懂换了一束百合,阿云一路捧在怀里,好一阵欢喜。后来,阿云就经常到陈庆阳这里,吃他炒的湖南菜。有一天她从后面攀上陈庆阳的肩膀,一头乌发下秀气的小脸贴上来,轻轻地说“我想留下来”。陈庆阳转身一把揽住阿云纤细的腰,这里婀娜摇曳、汩汩地涌动着滑滑的仿佛要抓不住的体香和热情……日子开始像飞一样。突如其来的小幸福的逆袭让陈庆阳有些反应过度了。他开始攒钱,变成同事眼中的铁公鸡,每次撮一顿以后他总是找各种理由赖份子钱。遭人白眼,自己一笑置之。说不清楚攒钱想要为了什么,他只感觉这些钱,包括自己的心冥冥中应当有个归宿。他跑超市更勤了,自己发现和一个居家女人没两样地往租住的房子陆陆续续搬进沙发、餐桌和其他小物件,逐渐填满了原来很空落的房间。直到有一天,事情发展到他开始删除阿云手机上客人的预约短信。终于被阿云发现。她夺过手机,愤怒地抿紧她的小嘴唇,扭身抛下那句冷冰冰的话,“陈庆阳,你想太多了。”
其实这之前陈庆阳并不是想太多,而是没多想。因为这句话,他真真正正地开始认真想起来,而且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觉得,人有时就像传说中有九条命的猫,寄身多个时空,有着不止一个的自己。他是,阿云也是。他和阿云注定只在周二下午这所泛着霉斑和湿气的房间里彼此能给予对方所需要的东西。超出此时此地,陈庆阳何曾真正认识那是怎样一个阿云,阿云也从来没有探触过那一个自己。也许换一个时空,彼此完全可能形同陌路、鸡同鸭讲。
看两人的关系真的到此为止了。可下一个周二阿云如期而至。她自己带来了小龙虾和非洲大鲫鱼,冲着陈庆阳一阵子坏笑,“知道你没买。”那天陈庆阳真的什么也没买,他哪里也没去。坐在门口的大榕树下,嚼了整整一袋槟榔。所以阿云进来的时候,他汗流浃背、脸膛酱紫,呼吸急促,一个翻身拦腰抱住阿云娇小的身体,嘴巴蛮狠地在她脸上摩挲、狂吻。阿云丢下东西,宛若青瓷般通透的肉体填满了狭小房间里最后的缝隙。这一刻,他们是那么的彼此熟悉和需要……
陈庆阳狠狠嚼了几口嘴里的槟榔,感觉无味得很,索性将渣子啐到脚下,右手拿起啤酒,咕咚咕咚一阵猛灌。
他淡淡地回想起了关于那次肥皂剧版真情告白的结局。同样在山顶,马路从这里下探山坳,进入密林。秋天的风空落落的穿过山坳,瑟瑟作响。因为没有音乐喷泉、大理石面的露台、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以及一枚聚光灯下的钻戒,没有这些布景,他的告白无法如期ACTION。女主人公也未能如约出现,穿着她白色的连衣裙,在脚下洒满花瓣。等来的是班主任,于是剧情嘎然逆转。他还算客气,抽着一根刚刚点上的烟,并不看陈庆阳,只是面无表情地发出刻不容缓的邀请,“马上跟我来一趟”。这种小学生层级的告状以及所引起的系列反应让陈庆阳木在原地,用了足足半分钟来纾缓他措手不及的囧态。半分钟后,他用了一个撒腿就跑的动作,令班主任始料未及地一直跑到了山顶。在那里,他用了整整一个下午考虑该把自己往哪搁的问题,尤其是那张已经火辣辣的脸。这足够让他更深切地感受到往年秋决犯人时周遭残存的阴冷。好事的同学常常说起山顶这个昔日刑场的典故。一次枪响之后,被处决的犯人突然挺尸,把拿个细铁钎子准备上前验尸的法医吓个半死。尸身也就势跌下山崖,挂在了半山的枞树上……这个秋天的告白就这样带着一股子幽灵般的阴森味道被埋进了陈庆阳的记忆深处。他暗自发誓要远离班上所有的女人。
结果不出半年,因为父亲的去世,他彻底远离的不仅仅是班上的女人,还有校园以及这座小镇。其实刚住进镇上米黄色的一排安置房,父亲还挺开心。结果刚开起来废品店,镇上就一下子增加了四五家,三个月收下来的废品还不够摆下小半个房间。家里没有地,没了退路,父亲在四月间的一个雨夜从三楼坠下,至死没有闭上一双灰暗的眼睛。出殡那天母亲已经哭不出声。她一直死死地抓住陈庆阳的衣襟,是绝望,也是期望。陈庆阳明白,自己已经是家中唯一的男人。
他没有再去学校。班主任赶集顺便来做家访,劝陈庆阳不要放弃高考。按他的成绩,属于仅具擦边潜质的三类种子。班主任一路吃着母亲腌的半坛子酸萝卜,对味道赞不绝口,渐渐把劝学的事情给忘了。临出门的时候起身擦嘴,才想起此行的初始目的,慌忙告罪一样的一连劝了陈庆阳好几声“来上学吧”,母亲已经提前一步站到了院子里。陈庆阳明白母亲的心思。人不能没了指靠,况且她还是个女人。他当天就把一本一本的教材和高考复习资料拿出来,通通卖给了街上的废品店……
夜已经深了,几处闻名遐迩的休闲区的暗红色灯光尽收眼底。隔得太远,看不清人影。但灯光一直若明若灭地招摇,温柔大度地接纳平等众生所有下半身的错误。这座城市的闻名一半来自林立的工厂,一半则来自这一片片招蜂引蝶的夜色温柔。有好事者曾经画了一张本市的寻欢地图,街区门牌路线一应俱全,看得陈庆阳瞠目叫绝……
那天夜已经很深,山顶有些凉,陈庆阳就这样一个人坐着想了很多自己过往的事情,喝了很多酒。想起下山,已经感到通身蔓延着阵阵寒意。登山步道的路灯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熄灭。自己感觉步子有些飘,略显迷离的眼神,凭着山脚城区投来的微弱灯光,已经辨不清路。他靠着一盏手机灯摸到山脚,错过了景区关门的时间,出来又错过了回租住的城中村最后一趟公交车。公交站的路灯久不擦洗,昏暗的黄光,照着一个单薄晃荡的背影,慢慢向城中村的方向踯躅而行。
这个背影并没有走到此行的终点。他止于一场意外的死亡。
一切因为一条狗,也许是一条白色的京巴。陈庆阳远远摇晃着荡过来的影子激怒了这只京巴。而它不断靠近目标的吠叫又激怒了酒精刺激下的男人。他直接拾起地上的一根小树枝,就势给了愤怒的小狗一记很奏效的教训。接着女主人出现。他们之间在一顿口舌交锋之后下了一个关于有种留下还是没种开溜的赌誓。他们谁也没有走。陈庆阳没走是因为他突然有了尿意。他只是觉得这事有些好笑,于是直接转过身,开始解裤子撒尿。这个举动很爽,但很不智。女人打电话叫来了男人。三个彪形大汉敏捷如鹰隼。陈庆阳拉上裤子的瞬间听到冰凉的血从后腰汩汩涌出……
陈庆阳最终安居莞城,再也没能回去。买墓地花了赔偿金的一大部分。下葬的那天,只有母亲。她没说什么时候再来看他。这里离家千里,舟车辗转,对于她怎么也算是一次过于昂贵的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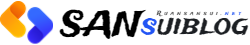




失落的羊9 个月前
研究计划导入公众号文章。
失落的羊1 年前
研究插件:挂载点研究、文件读写研究、API读取数据、设置、前台显示
失落的羊1 年前
今日申请十年之约博客成员!
失落的羊1 年前
启用新的访问统计.
失落的羊1 年前
重新整理长篇连载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