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hristy米娅
1.
圣诞节前一周,一行朋友以“购物和狂欢”为主题从捷克周边的几个国家赶来布拉格小聚。
见面那天是个星期五,天干地燥人心冷。大家先是三两成撮儿自由活动,到了饭点儿赶上心血来潮,临时决定围顿火锅儿。捧着手机反反复复几番商量,最后梁哥香烟一掐脚跟儿一跺——
“就在民族大道的中餐馆好了!”
大家长声短声一阵唏嘘,他这才轻咳两声,接着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我接到消息从家里直接出发,单枪匹马最先到达。没想到,就在那儿,又见到了失联已久的姑娘米米拉。
此时,她已经长发过肩了,亚麻色的轻丝在头顶挽了好看的簪,腕儿上的刺青也已经洗掉了,眼神明媚异常。她走过来亲热地抚了我的肩,温柔不改地咧开嘴冲我笑,一副风生水起的样子。
我愣在走道上,从头到脚地打量她。看了一遍又一遍——崭新的发型,崭新的面容,崭新的衣着,崭新的气色。目光连带着往边儿晃了晃,一位容貌带着九成新的男人正端立在她的身旁。
她没注意到我浑身自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惊异,侧了侧脸,雀跃似的挽过身边人的胳膊——这是我未婚夫,打个招呼吧!
2.
我的一个朋友,姓米名米拉。北京女孩儿,在布拉格电影学院学习电影海报设计。她的父母必定一早便料到了她要走上“艺术”这条不归路,才斗胆为她取了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怪名字。
米……米拉,读上去轻松惬意,但如果掌握不好节奏,唤起来像是打了结巴。
米米拉是我读语言班时候认识的姑娘,因为性情平稳温和处事善良正义,不到一年便横扫男男女女,顺风顺水晋级成了所有同学的好闺蜜。这姑娘样貌普通,智商平平,胸前无大,身后风平浪静。
没错,米米拉就是一个热热闹闹的“生活女配角”,而在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那么几个顶天立地的女一号。
然而唯一能够将她区别于路人甲乙丙丁的先决条件就在于,米米拉生性热情似火,天真起来整个儿世界一马平川,温暖起来拥有令八大行星驻下足来捶胸顿首的独门技能。
3.
真正和米米拉联络情谊,是在2011年的冬季。那时候,她已经申请上电影学院了。
我喜欢喝咖啡,正好她在城区大道的“兔子尾巴”咖啡馆兼职做侍应。在那段寒冷彻骨且前路模糊不明的峥嵘光景里,唯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周一、三、五下午放学后和她肩并肩坐在伏尔塔瓦河畔谈天说地连吸带舔星冰乐家庭装。我红唇香烟,刘海遮住半边脸,拉妹光环黯淡,嘬着吸管儿坐在正对面。我努力开创我的性感人生,她穿灰色高筒雪地靴,大脑清澈眼神无辜,俨然一位古道热肠的倾听者。
大家统统喜欢她,因为她是整个儿咖啡馆唯一一个不会在奶泡上拉花,却见人就会扬起嘴角微微笑的姑娘。
米米拉细胳膊细腿细眼睛,工作之余喜欢穿水洗旧的牛仔短裤和淡黄色棒针毛线衣,外面裹着件工工整整的枣红色呢子大衣,脚蹬两坨毛绒绒的灰色的云。一整段挺长的时间,她都与七八个制作小组的同学住在一间宽阔的前苏联式旧公寓里,睡抽去龙骨的床垫,吃拙劣的大锅餐和超市买来的冰冻披萨。那之中有志趣相投的好战友,有暗战不断的反面派,有私人空间感及其强烈的进修小导演,还有她心仪已久却全然不敢展开攻势的“小清新”牌台湾老男孩儿“亨利李”。
我总共也只造访过一次他们的住所。那是在一次大作业的关机派对上,米米拉左手香槟右手杵了杵我的肩,她醉意盎然地猛晃着脑袋——嘿,我就要搬家了。
那是她与梁哥认识的第三个星期末,也是梁哥失恋的第三个星期末。当然,后半段儿,他也是赶在分手的时刻才告诉她的。
梁哥在布拉格的一家中国公司作物流,是“兔子尾巴”的常客,那段时间天天光顾,西装革履,咖啡只点拿铁或espresso。
是米米拉率先动的心,可她不敢轻举妄动,她试着用巧克力酱在拿铁上面画桃心,画坏了一个又一个。直到有天结完帐,她转身就要走,没想却被梁哥一声拽住。他慈眉善目地指着杯子说,姑娘啊,你可真逗,我平生还是头一次见人在咖啡上画屁股。
米米拉当场怔住,眼睛瞪得老大。整个儿场面囧的蓬荜生辉,她却“吱吱呀呀”地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手无足蹈地解释了半天,好不容易换来一句话“今天有时间么?不如一起吃晚餐吧。”
这一年,米米拉22岁,初次恋爱,撞上了梁哥。
4.
米米拉搬去和梁哥一起住,在市郊租了一套六十来平的小公寓。房租平摊,生活费基本上由梁哥独自一人承担。虽然算不上富足,却也衣食无忧。他风雨兼程在外打拼,她也任劳任怨,课业之余做起了快乐的小主妇。
说起梁哥的爱好,灯红酒绿的食色大欧洲,可他偏偏喜欢吃火锅。米米拉虽然不好这口儿,却也总是欣然前往左右陪同。民族大道的中餐馆儿是大家聚头的指定场所,物美价廉不说,老板本就是成都人,菜品地道,汤料纯正。
大家围着桌子热火朝天吃涮锅,米米拉一定是忙到翻天的那个。梁哥着手涮牛羊肉,她就一筷子一筷子地给他烫;梁哥又要毛肚,她就拿个小漏勺守在锅边儿轮着番儿地等。梁哥说,年糕快煮化了,她就挽起袖子挨个儿往大家碗里捞,梁哥说,别光招呼我了,你自己也快吃点儿吧!她二话不说,笑盈盈地捻起一只大丸子,恨不得直接送入他口中。大家敲着碗筷大肆起哄,搞得梁哥满脸通红。
有一次领了年终奖,梁哥自告奋勇邀请几位好友吃火锅,不用想,拉妹自然紧随其后。席间大家依旧该闹的闹该乐的乐,嬉笑怒骂漫天八卦。饭局末了,我们几个差不多都喝得吊儿郎当了,梁哥大手一挥叫服务员来结账。正要掏钱,半道儿杀出了米米拉。她一把夺过梁哥的钱包,满面红光地叫嚣着“你的钱你留好,这顿我来慰劳大家好啦!”
梁哥立马拉她过去,伏在耳边说了些什么。没想米米拉用力摆着胳膊,“什么说好了你请啊?怎么这么啰嗦,咱俩谁出都一样!今天我来,如果你过意不去,下次跟我这儿补回来就行!”
这举动弄得梁哥好尴尬,他的脸由白转红,接着又由红转黑,一看拉不住,只好缴械投降。那天晚饭过后,大家扎堆儿去酒吧,他们两个借故推辞,一路沉默到家。米米拉催促他洗澡,他却坐在沙发上纹丝不动。她不明所以地上前帮他脱衬衫,却被他毫无意识般一手拦下,接着长嘘一口,“米拉,我想我可能真是有些累了。”
挺长时间后的一次小聚,不知是谁无意中又提起了此事儿。梁哥这才跟大家解释,拉妹在饭桌上虽然是万般好意,但这番举动,让他一个大男人的面子往哪儿搁呢?
毕竟正一同经历着好山好水好光景,一句“累了”兴许无以为患。米米拉想了想却也没当回事儿,该学习学习,该顾家顾家。
情人节那天,米米拉很好心地邀请我和另外一位单身姑娘去家里吃烛光晚餐。刚在客厅沙发上坐下没多久,梁哥就满身火气地冲了回来。他将手机往桌子上一摔,潦潦草草向我们问了声好,二话不说便将米米拉连推带搡地赶进了里屋。前言欠缺,后语不足。我和那位罩着一脸雀斑的单身女生全然猜不透发生了什么,只好手捧水杯我看看你你望望我。
屋内的争执声越来越大。不出二十句,战火全面爆发。雀斑姑娘被吓了一跳,周身一抖,水杯毫无悬念地滑落到了地毯上。她接着跪下身子不顾一切地拼命擦。还没等清理干净,就看见梁哥挺着个怒火朝天的大脑袋直端端冲了出来。他几步划过客厅,没顾上看我们,抓起外套就往门边走。米米拉在后面边追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玩儿命吼着,“到底谁对不起谁啊?你不就是忘不掉她的样子吗……”
我俩没去追,毕竟成年人之间的私事,是不怎么好干涉的。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也就不得而知了。我蹲下身子帮雀斑姑娘清理水渍,等到一切都安顿好了,这才讪讪离开了他们的公寓。
只是后来一次见到米米拉的时候,她的头发已经剪短至耳根了。除此之外,左手手腕处还多了一块儿莲花形状的刺青。那处藏青色的图案毫无美感可言,远远看上去,更像是一小片丑陋的伤疤。
就因为他说自己独爱短发的姑娘,就因为他说,如果你真的爱我,那就把我的信仰刻入身体啊。他信口胡言,她却当作真话来听。怪就怪,她总是费尽心思认真揣摩他说过的每一句话。
大家一方面心疼她,一方面又笑她傻。梁哥也就是个道路不明前途未卜的苦逼小青年,和这城市里众多潜质尚未被开发的劳苦大众一样,勉强维持着一份并不怎么合乎心意的工作。就这么一个普通人,你说你干嘛要对他俯首称臣唯命是从呢?
“你知道么,他对我而言实在太重要了。”那是与梁哥刚刚刚刚走到一起的时候。有一次,我下课后照例去“兔子尾巴”买咖啡。店里客人不多,米米拉趁老板不在,忙里偷闲在我的对面坐下。
那时候,他们之间的爱情还是另人神采飞扬的制氧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谈论起这段关系,总能引得她笑容满面容光焕发。
“我的性格中规中矩打小家教严格,之前没谈过半场恋爱。从青春期那会儿开始,也只是凭借着一部部言情小说体验爱情。到了真该找对象的年纪,害怕受伤不敢亲身试水,只好寄希望于一本又一本的’爱情鸡汤’。每每遇到看上去无比心仪的男人,第一反应便是回顾书本,对号入座,原地按兵不动,而后对对方的一言一行进行反复揣测。结果呢?却是每况愈下。不是我夸张,形容那段糟糕光景的词,无非就是什么颠沛流离啊,曲终人散啊,仿佛’孤独终老’注定了要成为我命运的最终定义。”
她一口气说完,停顿下来。两步跨去吧台,给自己倒了一杯柠檬水,又郑重其事般在我的对面坐好。
“直到我遇到了梁哥。”紧跟着一声轻咳,像是提醒着某种隆重的开场。
米米拉跟我说,那段时间的她真的是身心具疲有气无力,在爱情与虚晃的河流里苟延残喘地游啊游啊,拼尽全力却靠不了岸。梁哥绝对不是令她一见钟情的那个,但也算是接二连三在内心深处撞出了爱的小水花。她一开始其实没想太多,只是在他的咖啡上画桃心,与此同时和自己赌着。
“我没有任何伪装,也放松了警惕。扔下那些安慰日日夜夜的’爱情拯救论’,尽情发挥了好一阵儿。没想到,虽然画的桃心儿没被认出来,但情感道路反而畅通起来了。你们不理解我为何对梁哥万般好,那是因为我对他不仅有爱还有感激,感激他给了我一次放手去爱的机会,感激他让我知道自己值得爱与被爱……”
我将咖啡杯朝近处挪了挪,顶着满脑子的天马行空跟着附和:“谁说不是呢!爱情大道理基本等同于徒有其表的大白话。普天之下有那么多男人,又怎么可能整齐划一、详详尽尽分门别类呢?有的男人喜欢安逸,你过于折腾,他势必会与你分手;有的男人喜欢新鲜刺激,而你过于本分沉郁,他势必会与你分手;有的男人天生喜好同性,而你偏偏是位异性,他势必会与你分手。你看,这世界从来就不存在爱情的模范形式或最优定义。所谓的’爱情鸡汤’,不过是主观控制之下经过层层筛选,选出最符合自己心意的镇定剂而已。”
米米拉一手捧起水杯一手捂住嘴咯咯笑。她说姑娘,哲学院出来的讲话是不是都像你这样挥洒自如头头是道?
你们可能不知道,这其实是人生中的头一次,因为梁哥的倾情出场,米米拉放弃了“爱情鸡汤”这门死心塌地的终极信仰。
5.
就在人人称道米米拉是个宇宙限量版无敌贤内助的时候,梁哥却单方面提出了分手。理由是,你对我太好了,可我却力不从心,觉得压力很大。事实上还有一个更为具象的原因他没明说,认识米米拉的时候,他和前任刚刚分手。在上一段感情香消玉损的末尾还没来得及缓过劲儿,与其称米米拉为“新欢”,不如说她是一根会在奶泡上画出屁股型桃心的救命稻草。
梁哥也不是不爱米米拉,可人情世故儿女情长,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与前任相依相伴七年半,整个儿风光明媚的青春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对方。前任是个安静细腻的南方姑娘,言行举止轻巧而娇持。时光在梁哥的感情观里烙下了深而炽热的印记——那位终极伴侣,本应该是个温柔娴静与世疏离,微笑起来云淡风轻的南方姑娘。
可米米拉恰巧相反。对生命时刻充满了热忱,对生活怀抱着火一般的激情。这样的姑娘,换在懂得欣赏的人的手上,想必会是一件稀世珍品。
有天下午米米拉闲来无事,干脆和我约在了共和广场附近的一家披萨店。我提前五分钟到达,对吧台要了一杯热可可,一面搅奶油一面气定神闲坐在门边的位子上往街道望。不一会儿,米拉拉背着只环保袋出现在了落地窗另一侧。
我招呼她进来,抬手要了杯热可可,伸手朝她面前一推——暖身暖心,喝吧。转身又要了份土豆披萨。
那顿晚餐吃得相当艰难。拉妹面对质疑与安慰左右闪躲,我也只好讪讪笑着,面对主题三缄其口。
米拉中途去卫生间补妆,回来的时候鼻头红得像驯鹿。她用刀叉切披萨,却始终低着头,参差不齐的碎发挡住了鼻子以上的大半张面孔。我伸手去抚慰她的肩,她这才强忍不住哭出了声,豆大的泪珠“噼里啪啦”砸湿了面前酒红色的餐布。
“我曾几度认为,我们是彼此这辈子最最理想的伴侣,对此,就算情感触礁颠沛流离她也曾深信不疑。可事到如今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被自己的一厢情愿蒙骗了这么久。他对前任念念不忘,可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他想枕边人变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我头发剪了,刺青也纹了,他要什么,我统统愿意极尽全力配合。”她仰头将杯中的可可全部喝光,缓和了情绪,这才接着缓缓开口。
“后来我也想通了。要说,谁的初恋不是给给给呢?梁哥也曾义无反顾地给过,虽然......那个人不是我。但这么想来,心里总是要平衡很多。我知道,他不是不好,我也并不糟糕。只因为我恰巧不是他心仪的那一类姑娘。我才二十三岁,年轻得恰到好处。依旧热衷于满世界闯荡,而梁哥也依旧是我欣赏的对象......”
没过多久,米拉搬出了合住的小公寓。又过了一段时间,梁哥也搬了出来。一前一后的出走,令房东大为不解。可要我说,一定是在米拉走后,他不忍一人消受那段爱痛交杂的美丽回忆吧。
6.
一番不朽回忆,我在与米米拉左侧隔了一个位置的圆桌边坐定。服务员将菜单递上来得同时,门口响起了小团嘈杂的声响。晶晶拎着只硕大的购物袋首当其冲,短短的队伍,梁哥紧跟其后。正要入座儿,却一眼撞见了坐在正对面的米米拉。他立刻怔在原地,四目相对的戏码跟着上演。米拉万般尴尬地愣在那儿,惊异之余,只好微笑着咧了咧嘴角。梁哥正想要上前说些什么,那位崭新的男士算准了似的,端着两盘牡蛎春风满面地走了过去。
桌上的铜锅几尽沸腾,蒸汽升腾缭绕模糊了彼此的视线。她不再看他,转手将几片羊肉放入小勺,等了几口酒的功夫,从锅底捞出,再接二连三地往对方碗里夹。男人笑意盈盈地将橘子汽水递过来,她掩着嘴轻轻笑,眼睛里是数不尽的温柔。那场景似曾相识,感叹之余,梁哥竟感到有水汽涌上了眼眶。
觥筹交错的时刻,服务员前来对单,那目光险些被岔了过去。梁哥一个激灵,伸手抢过服务员手中的菜单,一笔一画认真核对起桌上的菜品来。
后来,他毫不自持地望过她好几眼,而她却始终忙上忙下热火朝天着。那次遇见也就不了了之了......
过了挺久,梁哥的身边又出现了一个姑娘。姑娘是西北人,大眼睛高鼻梁,烫得一头亚麻色的大波浪。朋友们一起吃饭,她做事周全,谈笑豪爽。最重要的是,她分好菜品往大家碗里夹的样子,简直和米米拉一模一样。
我抬头站在窗前,看着华灯初上的民族大街。是谁说善良的女孩儿得永生来着?米拉,你看,布拉格下雪了,北极熊也该冬眠了。你遇到能够相拥一生的理想先生了,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好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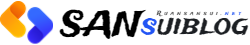




失落的羊9 个月前
研究计划导入公众号文章。
失落的羊1 年前
研究插件:挂载点研究、文件读写研究、API读取数据、设置、前台显示
失落的羊1 年前
今日申请十年之约博客成员!
失落的羊1 年前
启用新的访问统计.
失落的羊1 年前
重新整理长篇连载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