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宝骑鱼
中国人普遍爱吃豆腐。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结尾处感叹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话中充满了一个在政治上屡遭挫败、却仍然心怀天下的固执文人的民族自豪感。
豆腐说来历史悠久,为汉武帝的叔叔淮南王刘安所发明。之后,从王公到百姓,无不爱戴。做法吃法也是花样百出。千百年来,在中国餐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解放前,据说,乡间豆坊并不天天开磨。如有客户上门订购,押下订金,豆坊师傅才会备好材料,四更时分,掌灯生灶,蒸豆磨浆,滤渣点卤。这豆腐是嫩是老,全在这点卤的学问之上。手浅了,成了豆花,手重了,成了豆干。
我童年时的县城,老街上有爿“方家豆腐”,据说从清末就有了,是家百年老店。每天早上,方家最小的儿子会挑着豆腐花和卤豆皮出来卖。挑子上带着碗筷蘸料,人们可当街吃一碗葱香辣子豆花,或是白糖豆花,只需要付一毛五分钱。
这方家小儿子,人长得就像这豆腐,白白嫩嫩,眉清目秀,可戏可欺的俊唐僧一般。我表姐那时正是闺中待字。每天都到巷子口去买一碗豆花喝。出门前,她会用桂花水梳头发,一丝不苟地压成麻花辫。鼓着嘴巴把流海吹翘起来。嘴唇再用力抿几抿,使唇色红艳自然。衣饰上还总要配个围巾,或在手腕上绑个红丝带,整个人显得俏丽出挑。
在豆腐挑子旁,表姐会故意慢慢地喝豆花,一小口一小口,背靠在墙上,腰细得不盈一握,到了臀部那里又突然丰硕起来,好看的腰身全送进了别人眼里。十几分钟光景,一个小瓷碗还掬在手里,红色的丝巾垂在细白的手腕上,不时用它擦一擦唇角。方家小儿子不知觉便看呆了,等知悟过来时,脸羞得绯红如霞,收钱都不敢抬头。表姐便得了逞,笑得一串银铃般跑回了家。舅妈问她干什么疯癫成这样。她说,吃了一碗甜豆花,甜到心里去了。
后来舅舅舅妈做主把她嫁给了一个远方军官,在外生儿育女,冬去秋往,甘苦自知。
她给我写信,说北方干燥,人糙,连豆腐都是硬绑绑的。她想家,想南方的温润柔软,想老街的甜豆花。
有年冬天,她突然独自跑回来。家里人也不敢问也不好劝,偷偷给那边通电话,原来是吵了架。表姐则独自去了老街,发现豆腐坊变成了烤鸭店。再问起方家人,已出外经商,人去楼空。她寻到另一处豆腐店买了豆花,回家吃着,吃了半晌,非但没笑,反而垂泪。郁郁几日,便坐上返程火车,回到了她的丈夫和孩子身边。
她再给我来信说,才几年功夫,骨头变了,南方的冷雨让它生疼,只好重回北方。她忽然发现自己两头落空,在哪里,都是个异乡人。
再往后许多年,她在北方小城里开了一家豆花店。据说生意不错。体型也变得珠圆玉润,以前倚在巷子口妖娆俏皮的女妖精、担着豆腐挑子走街串户的俊唐僧都已遗落在岁月里,不知所踪。
我看过摆放在舅妈床头的表姐全家福,那是某年春节,她们全家老少穿着毛衣坐在炕上吃年夜饭的光景。满席佳肴,菜炉子水汽氲氤。家人脸上亮堂堂的,如附莹光。贴着窗花的玻璃窗外,飞雪静静飘舞。俨然一张现世安稳,天长地久的安居图。
现在表姐总说,她有两个家乡,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她呼吸着北方粗犷的空气,把那份温柔细腻像甜豆花一样随身携带到她所至之处,如同携带她那无可替代的青春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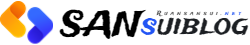




失落的羊9 个月前
研究计划导入公众号文章。
失落的羊1 年前
研究插件:挂载点研究、文件读写研究、API读取数据、设置、前台显示
失落的羊1 年前
今日申请十年之约博客成员!
失落的羊1 年前
启用新的访问统计.
失落的羊1 年前
重新整理长篇连载栏目